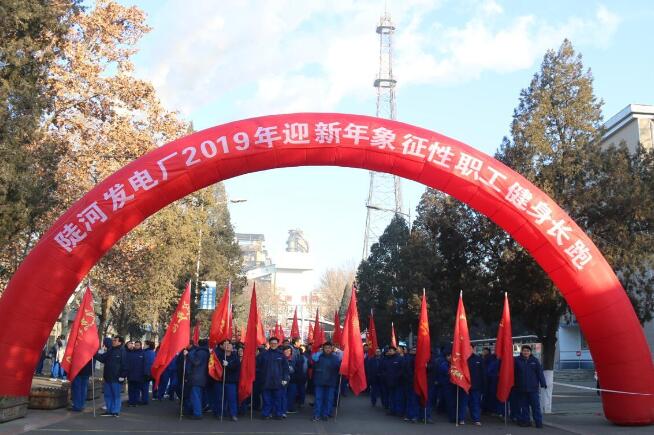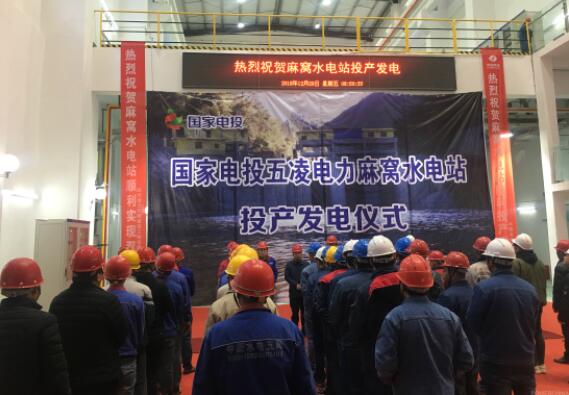猪栏鸡埘和柴房是每家必有的附属建筑
猪是必定要养的,再贫苦的家庭也得养猪,因为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得杀年猪。过小年到二十九吃的全是猪头猪脚猪下水,大年三十晚上的团年饭,猪肉和鸡是当家菜。还得熏一些腊肉挂在灶的上方,来了贵客就搭着凳子割一块,端午和中秋也全靠腊肉打打牙祭 。
养鸡也是必需的,洋火洋油盐全靠鸡蛋换,鸡屁眼就是农家的小银行。过年过节祭祀做寿走亲戚都少不得鸡。
孵小鸡是外婆的专利,别人不能插手。
把每一只种鸡蛋对着煤油灯照一照,透光查看是否新鲜,然后交给咕咕叫的抱鸡婆。一个多星期后外婆会从抱鸡婆肚子下面把鸡蛋掏出来,放到温水盆里,如果鸡蛋在水里偶尔摇晃一下,蛋里的小鸡肯定是活的,否则就是寡蛋(坏蛋)。三个来星期后,毛绒绒的小鸡便破壳而出。
每年要孵两次小鸡,春天一次秋天一次,春天孵的小鸡叫春鸡,秋天孵的小鸡叫秋鸡。年年守着外婆孵小鸡,久而久之我也把这本事学到了手,后来下乡当知青派上了用场——知青组里我负责孵小鸡,到社员家借抱鸡婆,还用母鸡孵小洋鸭子,成活率都蛮高的。
三四岁的时候,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鸡窝里捡鸡蛋,外婆会交代哪几只母鸡当天会下蛋,我就盯着那几只母鸡,看到母鸡蹲进鸡窝了,就守在鸡窝旁,我和母鸡大眼瞪小眼,那呆萌的样子一定很好笑。只要母鸡跳出鸡窝咯咯哒,就用极快的速度捧起热呼呼的鸡蛋飞跑去交给外婆。
在我的记忆中,外婆家是养了猫的,不需多,一只猫足以镇住祖屋的老鼠。不知什么原因似乎没养狗,邻家也没养狗,或许是觉得八元堂民风古朴,毋须额外费粮养狗防盗贼。
通向河边是菜园,那是外公的地盘。
田里的活计外公不怎么拿手,种菜却是八元堂的一把好手。菜园子就那么大,有两样东西却是少不得的——旱烟和苎麻。
那年头卷烟是奢侈物品,上等人才有资格抽烟卷,城里人一般用废报纸卷喇叭筒,七八十年代才流行自己手工制作卷烟。乡下人还是习惯用烟袋。
菜地再紧张,外公也会腾出一块地种旱烟。那玩意儿特难伺候,幼苗期怕太阳晒,白天得用大树叶盖上,傍晚时要揭开树叶让烟苗喝露水。烟苗长高了烟叶长大了,就忙着捉烟虫。啃烟叶的烟虫肉嘟嘟的翠绿翠绿的,跟烟叶一个颜色,要睁大眼睛才能找到。这时候,外公必定带我姐去菜园,小孩眼尖,一捉一个准。日出之前烟虫会趴在叶子表面,比较显眼。太阳出来后,这些肉肉虫就躲到了叶子背面,很难找到。捉烟虫那段时间,姐姐是睡不成懒觉的,除非阴天或下雨。
菜地的另一端必定是苎麻地。对于农家,苎麻很重要,捻麻线织蚊帐搓麻绳纳鞋底都少不了它,细腻的耐磨的绳索如牛綯秤盘索等等,必须要用苎麻绳,其他如箩筐等则用棕绳,走亲戚的精致的小皮箩或挑箱还得用苎麻绳。
春末夏初,苎麻长高了,用竹竿在地里使劲垂直抽打,叶子打个精光剩下光秃秃的麻杆,贴地砍下来,一折两段褪出白森森的茎,留下绿幽幽的外皮浸泡在水塘里。
外婆搬条椅子坐在阳光下,腿上摊块隔水的油布,左手捡起一条湿漉漉的麻皮,右手握刮麻刀,刀刃紧贴麻皮向外使劲一挥,“哧”的一下,绿色外皮应声掉落,留下白花花的麻纤维。正反两面前后两段如此反复四次,一根麻杆才算刮完。刮出来的纤维要在水塘的石板上反复捶打漂洗,挂在竹篙上晒干。捶打漂洗很有讲究的,必须理顺纹路,绝对不能搓洗的,一搓就乱了,搅成一团,再也别想理出个头绪来,所谓“扯麻纱”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
砍了的苎麻又会生长,一年能砍三次,有“头麻黑脚二麻黑腰三麻结籽”的说法。论质量,头道麻是最好的。
刮麻的时候,兴奋的还是我们。一群小孩跑来跑去抢着帮外公抱麻杆运回家或者给外婆递麻杆,很卖力的样子。
乡下居家,必得有水塘。
祖屋地坪前有两口塘。
一口是牛用的塘,队上的牛洗澡拉屎拉尿都在那口塘里。
另一口是人用的塘,女人们洗菜洗衣洗傢俬,男人们洗农具洗澡游泳,孩子们摸鱼“打泡求”。
五羊坪人喜欢狗刨式游泳,两手同时在胸前向后刨,双脚交替打出水面,“噗通”“噗通”水花四溅,很有节奏感,速度却极慢,谓之“泡求”。
塘里养了鱼,是公家的,但孩子们可以摸鲫鱼,因为鲫鱼不是养的。鲫鱼喜欢躲在岸边树荫下或石头缝里,蹑手蹑脚顺着塘底摸去,一抓一个准。有时候鲫鱼溜到塘中间,小伙伴们就争相扎猛子,鸭子似的倒立在水中,两只小脚丫在水面晃动。
那年头没有电没有汽车,小孩子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水,河里塘里都能淹死人的,因此绝对不许小家伙们私自到塘边河边玩耍。
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,濛濛细雨的春天,表哥在塘边钓鱼,我溜过去捉蜻蜓,脚下一滑,噗通一声摔到塘里,瞬间就没了顶。表哥听到水响猛一回头,只看到一缕黄毛没在水里,毫不迟疑跳进塘里伸手拽住那一缕时隐时现的黄毛,直接把我提溜到岸上。幸亏表哥救得及时,只喝了三两口水。外婆受了惊吓,外公把表哥骂的不轻,我偎在外婆怀里瞪着惊恐的眼睛瞅着发脾气的外公。
吓归吓,骂归骂,塘边还是要去的。装籇定鱼钓青蛙,摸鱼洗澡“打泡求”,水塘的诱惑力太大了。
大人们也知道,拦是拦不住的,只是约法三章:不许一个人去塘边,不许在水里开玩笑,下水游泳必须要有表哥表姐看护。
这些条件不苛刻,鸡啄米点头就是了,当然知道犯规的后果——楠竹桠子炒肉。

主办单位: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 网站运营:北京中电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:400-007-1585
项目合作:400-007-1585 投稿:63413737 传真:010-58689040 投稿邮箱:yaoguisheng@chinapower.com.cn
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》编号:京ICP证140522号 京ICP备14013100号 京公安备11010602010147号